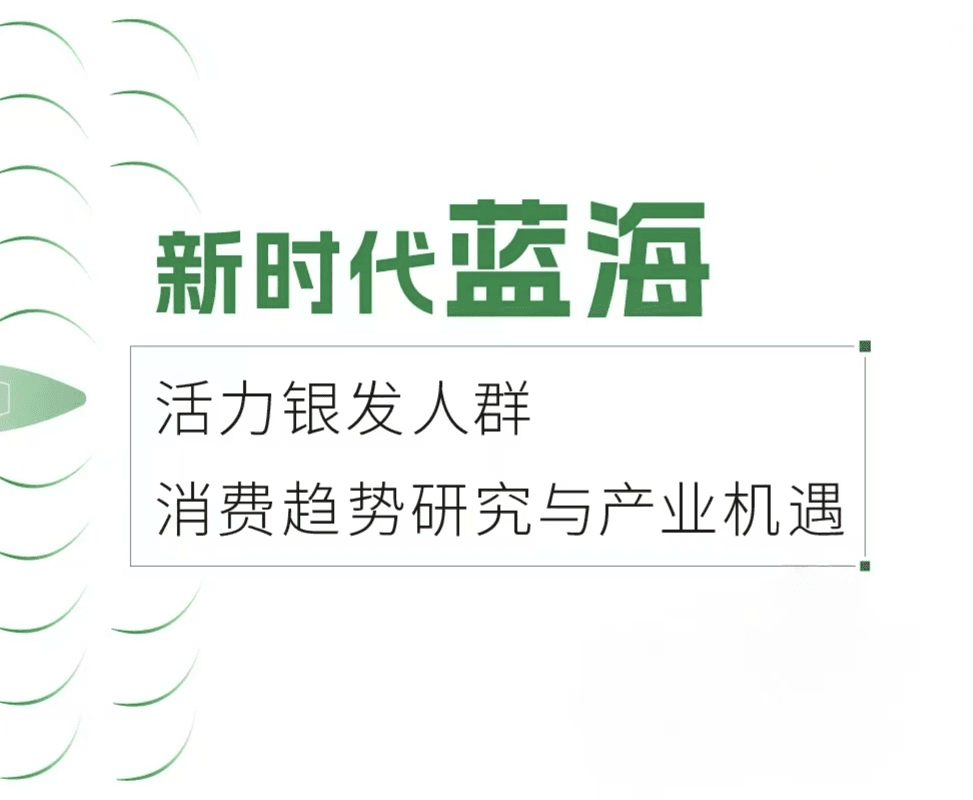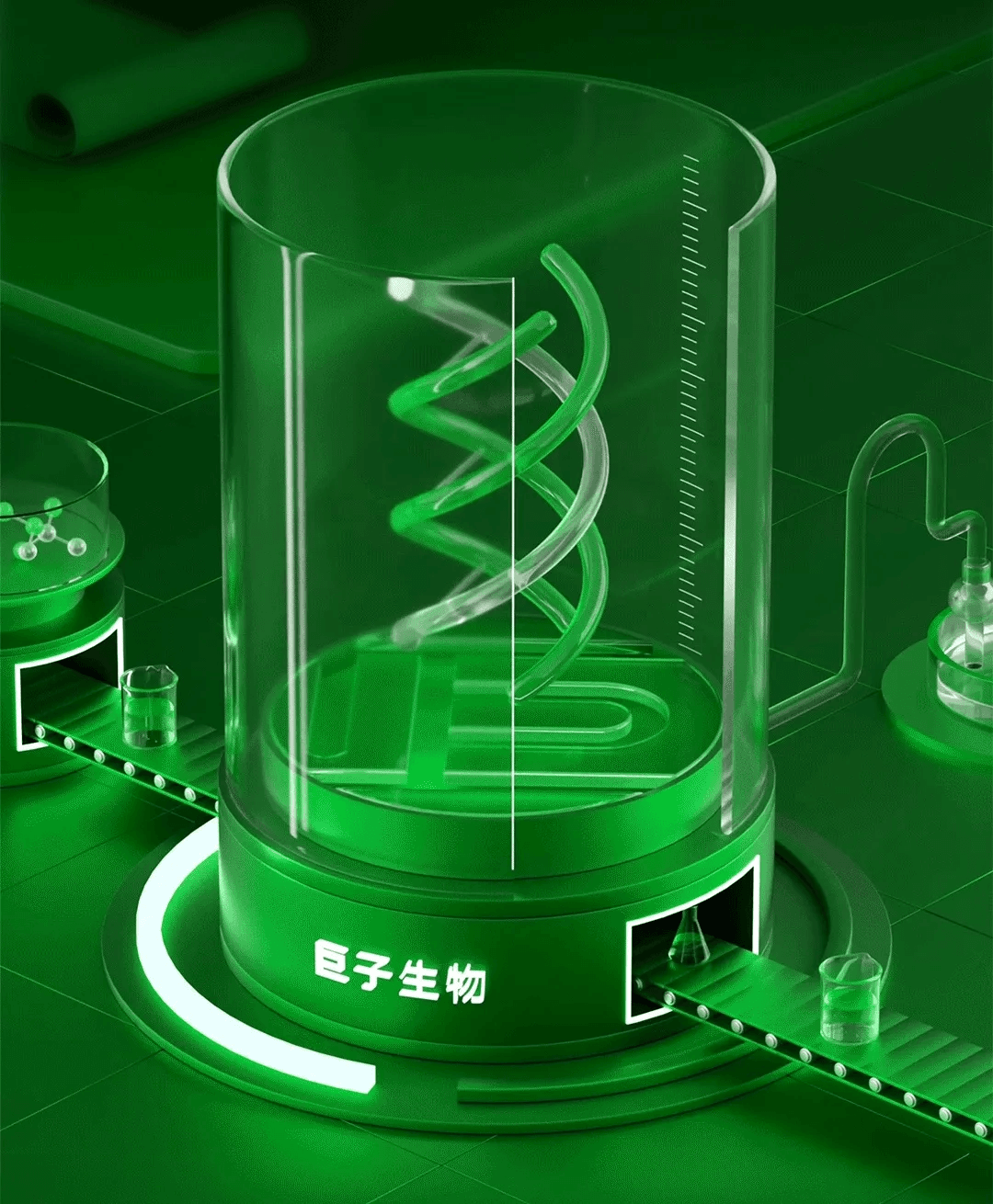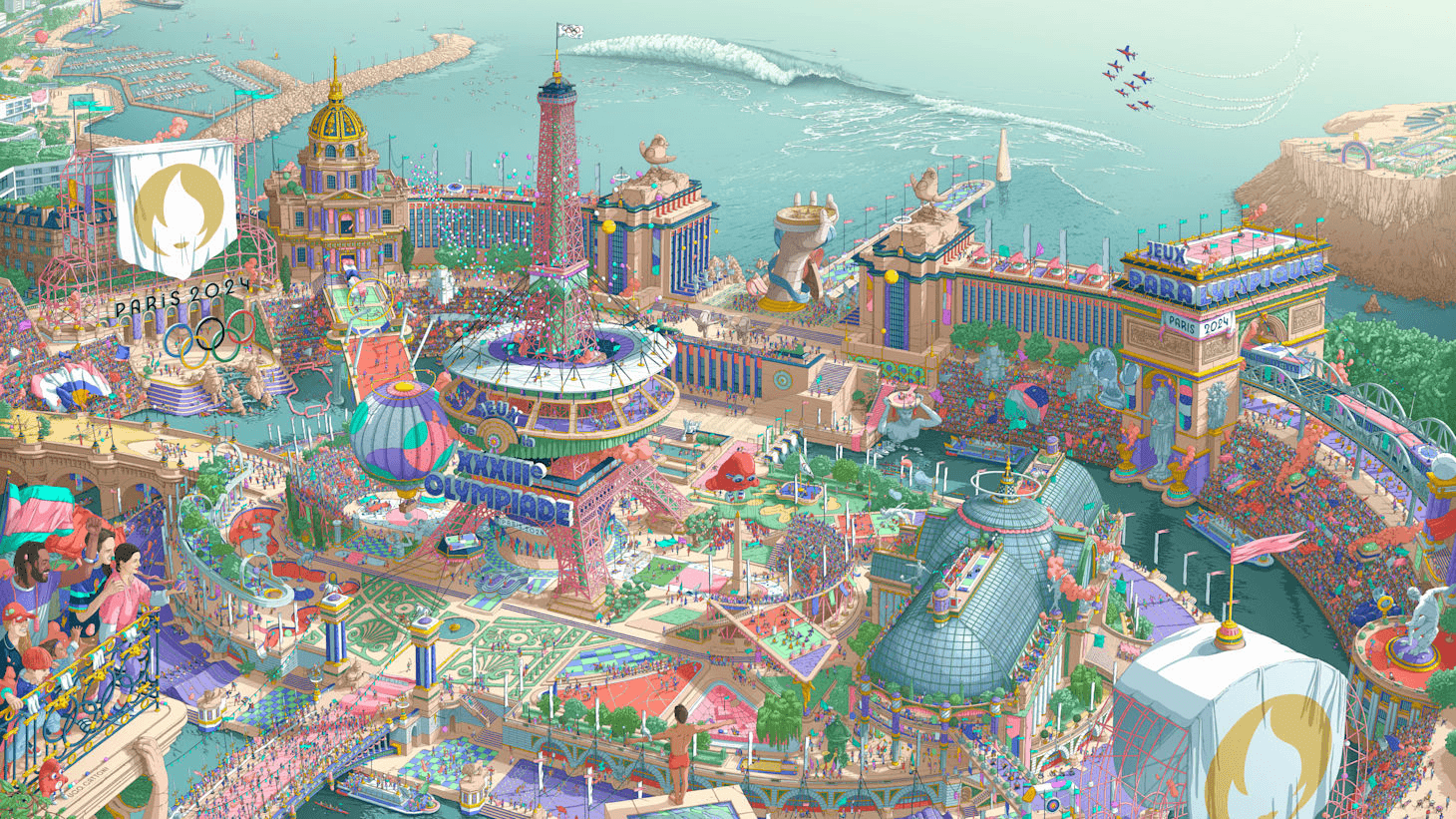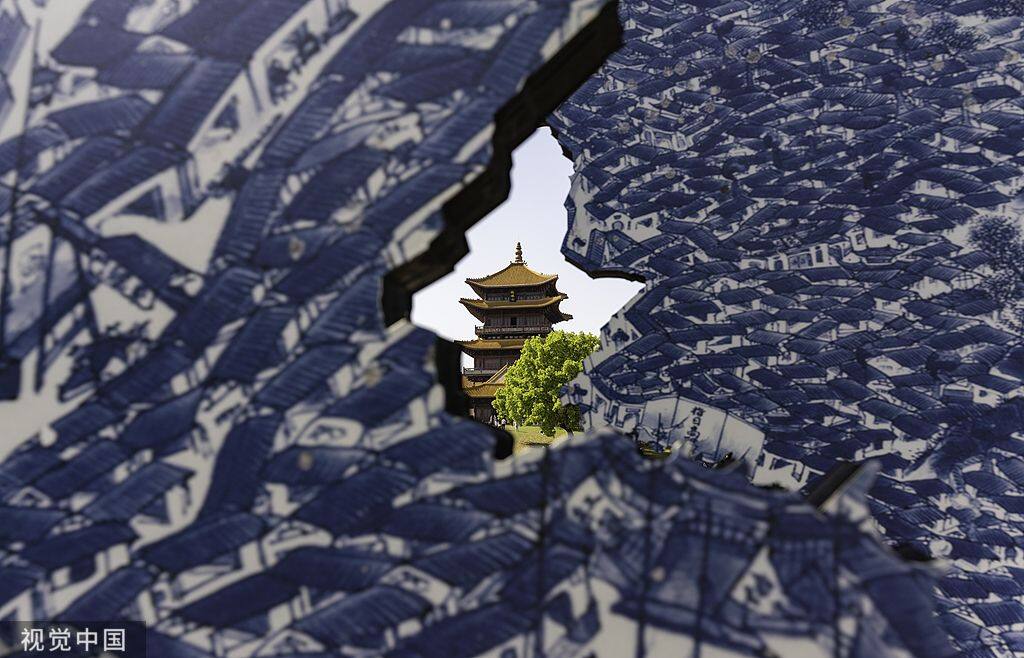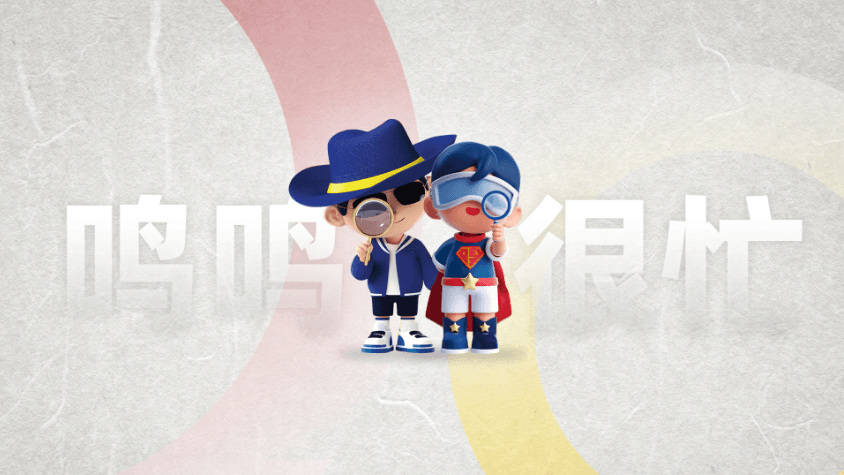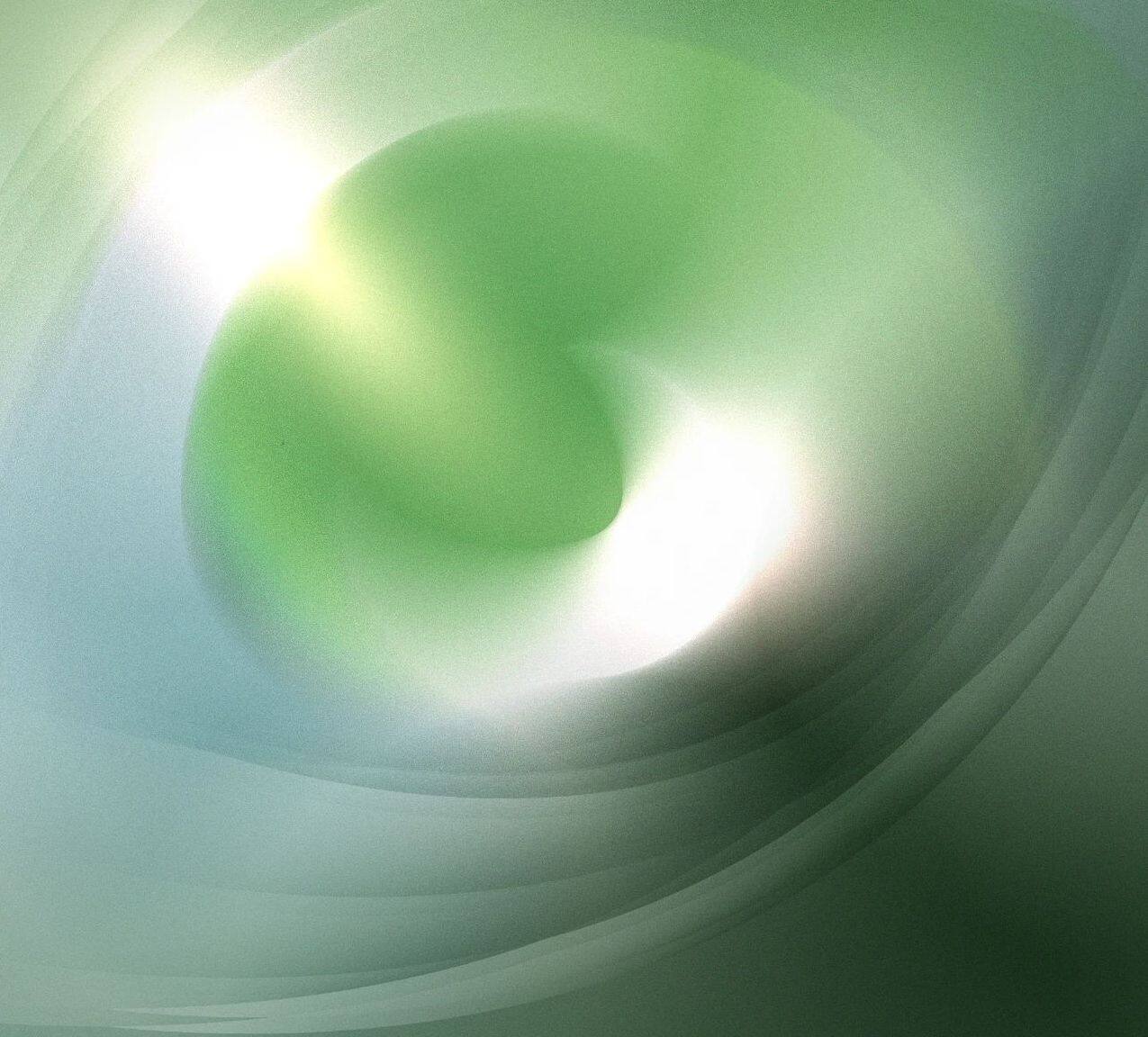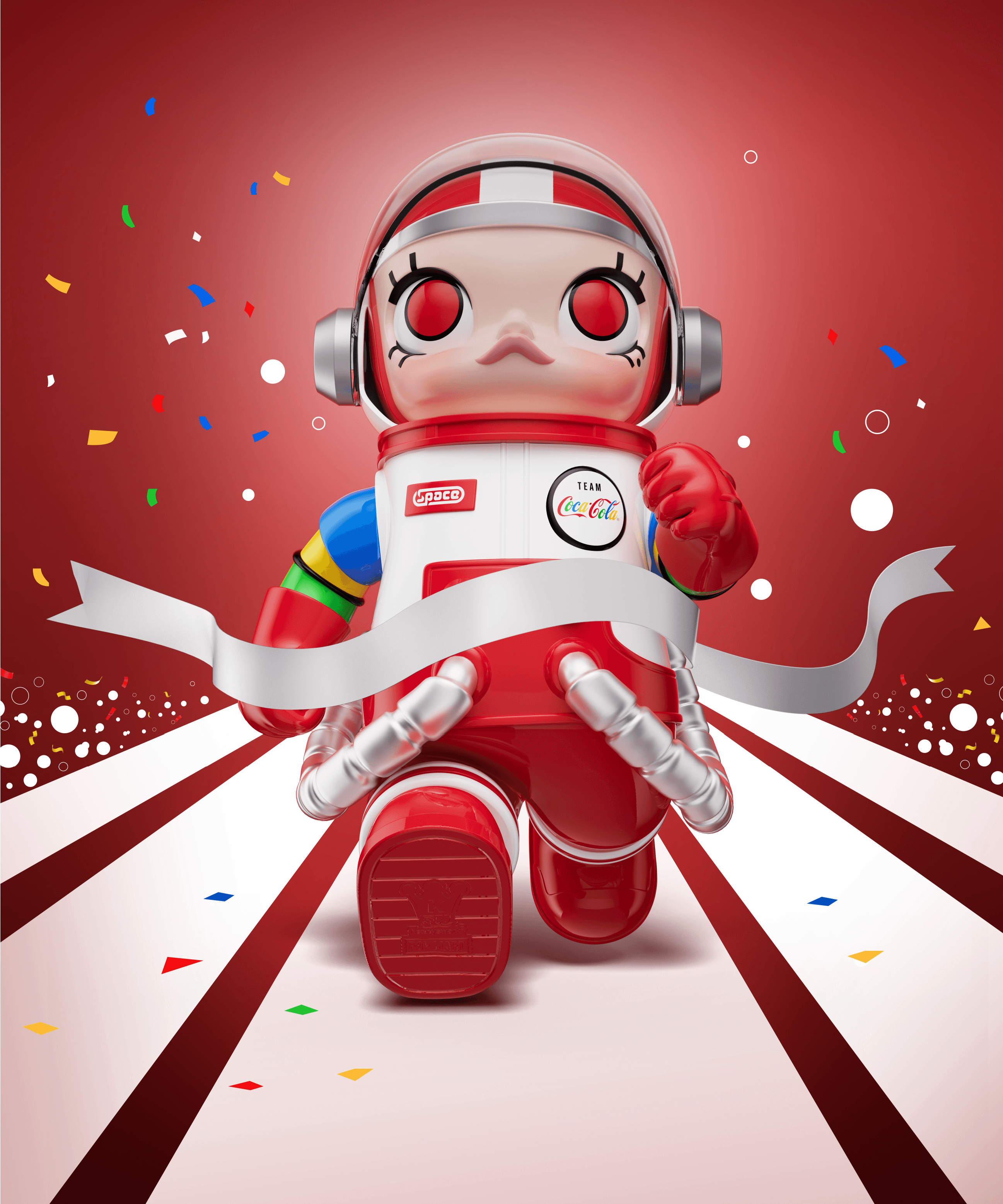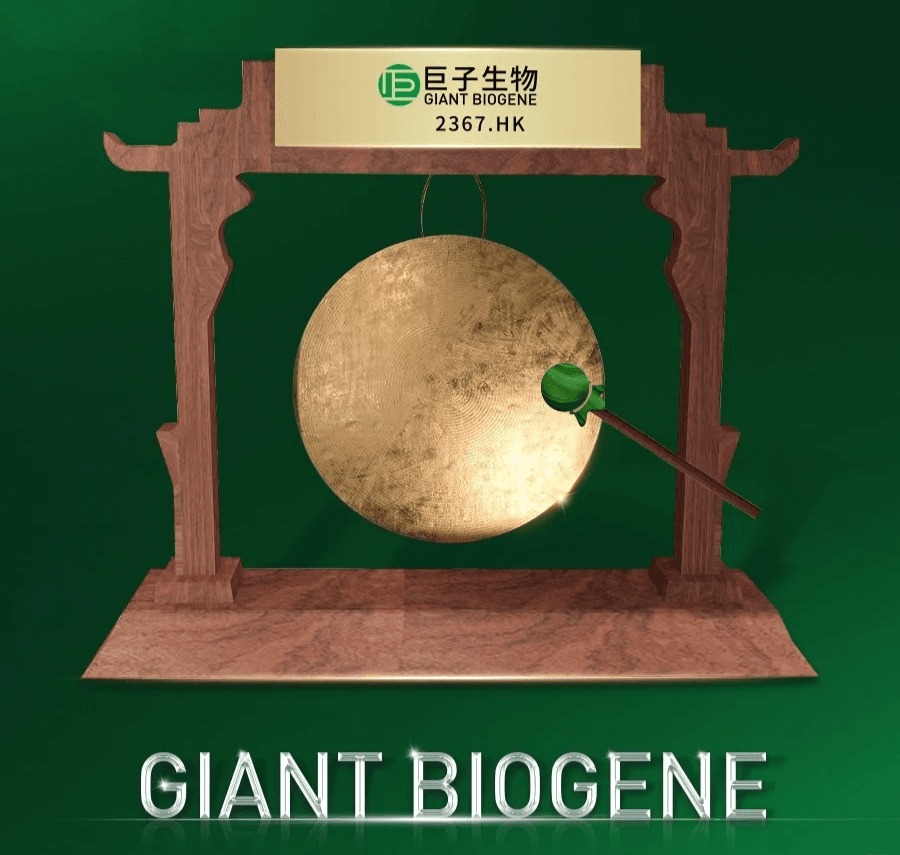编者按
这是黑蚁资本创始合伙人何愚2025年底的一份“田野笔记”。过去的一年里,何愚和黑蚁资本的团队走到了广东佛冈、湖南汨罗、河北安国等地的县镇街头,去发现一个个不在主流语境里的故事。
这不是黑蚁资本第一次在县域的街头“扫街”了。2021年到2022年,黑蚁团队就曾深入495个县域,带回了一份在创投圈引起不小反响的县域研究报告。
那为何在三年后重返?何愚认为:县域市场离一线城市太远,如果不花大功夫扎下去,就会失去对中国消费低线城市的“体感”。而投资消费所需的洞察往往是极细微的,甚至是要扎入消费投资人潜意识的。
这种“体感”在过去几年为何愚和黑蚁资本带来了巨大的职业回报——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即将上市的鸣鸣很忙。
2022年,黑蚁团队在县域街头看到了赵一鸣零食。那是一个完全长在县城里的公司,创始人赵定本人就生活在那个市场,最懂那个市场的用户。当时,黑蚁基于县域调研的逻辑推演,算出零食集合店背后是一个3000亿规模的巨大业态,足以改变整个休闲食品行业的供应链。这种认知支撑了黑蚁此后对于赵一鸣及鸣鸣很忙的押注。
最戏剧性的时刻发生在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的合并。在两位创始人的主导下,两周内完成了合并的所有事。包括黑蚁资本在内的老股东没有尽调报告,没有第三方审计,全凭对行业数据的理解和对创始人的高度信任支持了这一决定。
在何愚看来,黑蚁能有这种“敢于为模糊买单”的底气,除了对公司管理层的信任外,本质上来自于黑蚁看到鸣鸣很忙具备激发并满足县域市场需求的独特能力,而县域市场的需求是巨大的。 他认为,县域不是一线城市的简单复刻,它有自己的商业逻辑:那是一个高自有房率、低贷款比例、有着紧密社交网络和“熟人社会”韧性的市场。这种稳定性构成了中国消费最坚实的缓冲层。
不论是这一次重返县域,还是三年前的研究,参与其中的主力都是黑蚁资本的一线投资人们。何愚认为,投资机构绝不应该设立专门的研究团队。“一旦分工,就会削弱投资团队的研究能力。研究必须内化为投资人直觉的一部分。”
以下就是何愚和团队基于《2025重返县域研究报告》所撰写的5000字田野笔记。它记录了一家深耕消费的投资机构在中国最广阔的基石市场上,如何穿过宏观叙事的迷雾,去捕捉每一个微观生命的努力与追求。这份笔记不仅关于消费或投资,更关于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以及我们该如何理解所处身处并热爱的中国社会与人民。
本文首发于「暗涌」栏目「2025尾声」
写在前面
在正式展开系统性调研之前,我们先去了广东佛冈、湖南汨罗等地走访,想通过“扫街”的方式,先感受一下四年后县域市场的变化。
在两地随机进行了一些居民访谈后,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房子”在日常对话中并不突出。当地自建房较多,虽然实际房价有所下跌,但居民对此的感知并不强烈。如果居民的职业与宏观经济联系较大——比如物流或地产下游行业——那么近几年的收入确实受到了影响。
但县域的生活也有它缓解压力的一面。在佛冈,县城往外走不到五百米,就能找到一碗不到5元的面条。夫妻经营的奶茶店,用“可乐+冰,五毛一杯”的方式,应对蜜雪冰城这样连锁品牌的竞争。
我们在长沙吃过一碗8-9元的粉,但在县城看到4-5元带肉的面的时候,还是有更真实的冲击和思考:一方面,会本能地计算老板怎么赚钱,客流量、客单价、厨房几个人等等;另一方面,想起几年前我们在内部推演过,“如何把一碗面做到18元以下来打开市场天花板”,但后来吃过长沙的粉、县城4-5元的面后(差不多上海25年前物价),对连锁的理解又深刻了一些。
在汨罗,主街超市的商品种类虽然丰富,但价格偏高,陈列和选品也相对滞后。当地商业业态仍然比较单一。从这些细节来看,规模化、标准化的连锁业态——无论是更高效的超市,还是地级市的特有的业态——在县域依然存在明显的渗透与升级空间。
 五毛一杯的“可乐+冰”,摄于广东佛冈
五毛一杯的“可乐+冰”,摄于广东佛冈
这些碎片式的见闻,像一个个触点,让我们再次确认:县域市场有它自己的生活节奏,县域的商业也是如此。
随后的半年里,我们开始了系统的调研。我们回访了上次研究中的6位受访者,再次走了一遍他们生活的县城。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基层市场,这次研究新增了3位住在乡镇的受访者。同样,在定量部分的1000份问卷里,特意覆盖了30%的乡镇样本。我们想去更基层的市场看看,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
这一次的田野调研分为三个线路——华南、华中、华北,我们分别走访了福建诏安、广东四会、广东清远三坑镇;湖北石首、湖南湘潭;河北安国、山西临县碛口镇、河南安阳白璧镇。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在定量调研中采用了与2022年一致的核心问题与量表,并对两次调研的样本结构进行了校准处理。
先谈谈变化
- 满意度:个体的波动与总体的稳定
回访的6位居民中,有的受访人在过去三年间成为了妈妈,有的受访人迎来了自己的第2个孩子,而他们也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了比三年前低的分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生阶段的转变有关——在县域社会,人们普遍更早地进入了承担家庭责任、养育子女的时期,可能正处在“U型幸福曲线”的压力区间。
从覆盖更广的定量数据来看,县城居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并未出现显著下滑,基本保持了稳定态势。
- 体感压力:更常被提及的“经济压力”
在田野访谈中,“经济压力”这个词被受访者主动提及的频率,比三年前更高。这种感受也直接反映在他们的支出选择上。
尽管家庭总开销在增加,但他们在压缩个人非必要支出,尤其是那些带有“中产身份标签”属性的消费。福建诏安的受访者是一对夫妻,2021年妻子还会和我们分享丈夫送她的轻奢包,但这次她给我们分享的是她出门带娃拎的奶茶袋。“身份象征”的溢价正在减弱。
- 支出转向:压缩身份消费,保留悦己体验
但他们并非一味节衣缩食,为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健康的品类保留了预算。例如,广东三坑镇的受访者,住在还未粉刷墙壁的红砖自建房里,同时她也是400元/次瘦脸针的用户。此次回访中,唯一一个家庭收入有所下降的湖南湘潭受访者,她每周做4-5次瑜伽,年卡1000多元,她认为这项支出性价比很高,让她感到状态更好。
- 一个矛盾:体感收缩 vs. 实际收入
与更频繁提及“经济压力”的一个对照是:在回访的6个家庭中,有5家的实际总收入是稳定甚至有所提升。定量数据也显示,县城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水平在近三年并未发生显著波动。并且,他们对未来2-3年的收入预期仍偏向谨慎乐观,六成的人认为未来收入会增长至少5%及以上。
- 核心变化:是预期,而非收入,在改变消费
我们认为,县城居民所表达的“经济压力”更像是一种“体感收缩”—— 是由宏观叙事、地方企业波动与周遭氛围共同渲染的“体感收缩”。
这种感受更多源于对宏观环境与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变化,而非当下收入的真实下降。正是这种被调低的预期,而非缩水的钱包,在引导他们更加审慎地花钱——减少为了“面子”和“符号”的消费,同时却愿意为能提升日常幸福感的具体体验买单。
几组具体的生活切片
- 工作节奏:变得更忙了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县城的人们感觉工作节奏变快了。相比2022年,感到自己处于忙碌工作状态的比例显著上升,接近一半,2022年则三成有余。过去那种“有忙有闲”的节奏,正转变为更持续、规律的日常忙碌。
- 城市迁移:对大城市的向往减弱
考虑搬去大城市的县城居民比例有所下降。过去三年,表达“考虑过”的县城居民,其内部出现了态度分化——从“考虑但没想好”的状态,分流至“完全不考虑”或“考虑但是不行动”的状态。
大城市的边际吸引力在下降,大家不再是一味向往,而是会综合权衡收入、成本与家庭现实。福建诏安的受访家庭就谈到,虽然希望孩子去厦门读高中,但距离和现实让他们还没法决定。但由于稀缺资源决定了人口的流向,教育、医疗、产业等等,这并不改变长期的人口向更大城市流动的趋势。
- 房产:重要,但对心态和消费的影响有限
县城居民的房产以自住为主,贷款比例相对较低,这一点和三年前相比变化不大。整体样本中,超过半数的房产购于2020年之前,近九成受访者在过去三年没有进行任何房产交易。
访谈中我们也发现,尽管多数人知道房价在跌,但实际感受并不强烈。如果打开他们的小红书首页,再对比我们自己的,房产话题的推荐率完全不同。
- 婚姻态度:经济安全是重要的前提
县域居民对婚姻的态度务实、理性,但不具强制性。经济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可以结婚,但需要先有坚实的经济”是第二主流的态度(占35%),反映出经济安全感在婚姻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这一点在县城男性与乡镇男性之间的差异更能说明。乡镇男性表现出更深的经济焦虑,对“需要经济基础”的诉求最强(37.7%)。县城男性则更倾向“顺其自然”(41.6%),这一比例高于县城女性,也是所有对比组中最高的。
 当地最大商场设在一楼角落的“脱单便利店”,摄于河北安国
当地最大商场设在一楼角落的“脱单便利店”,摄于河北安国
我们如何判断机会
- 体验型消费的萌芽
在黑蚁投资模型里,我们将所有的消费类型分为效率型与体验型。
效率型消费 追求以更少的(金钱、时间)成本获得更丰盛的商品,通过量化标准(如性价比、时效性)实现生存资源的精细化管控。
体验型消费 追求真正的独特性,是在追寻体验世界和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消费行为(产品或服务)。
从县域消费者的闲暇选择能看到一些变化。疫情后,他们减少了在家看电视、看书,更多走进了电影院、棋牌室。虽然基数还不大,但开始尝试个人爱好和短途旅行的人变多了。这透露出,他们对个性化、体验式的休闲,有了更多兴趣。
收入依然是县域消费者尝试体验型消费的主要限制。但如果我们只看到他们最终选了低价商品/服务,就断定他们“只要便宜”,那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县域市场的供给,往往不仅在数量上有限,在质量和层次上也较为单一。
在县城一家新开的名创优品里,一个女孩对着货架上的彩色保温杯看了又看,表情里的欣喜是非常真实的,就像是在一线城市遇见一家精致的买手店。这个时候我们理解了,有时候由于业态的供给不足,在一线城市习以为常的品类类目,真的能够带给不同线级的消费者,发自内心的欣喜和快乐。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能,很多时候,县域消费者面临的不是“选贵的还是选便宜的”,而是“只有低价、且体验都差不多”的选项。当所有选择都挤在低质低价这一端时,价格成了最显眼的标签——这本质上是优质供给缺失下的一种被动结果。
当我们在谈论一个业态的爆发增长时,我们总认为“爆发的需求刺激供给的增长”,但真实的情况是,“创新的供给唤醒萌芽的需求”。一个品类能否在县域市场真正渗透,关键在于供给能否清晰定义价值、并降低获取门槛。
平均月收入3300元左右的县域消费者,需要的未必是极致独特的“精品体验”,而是价格可接受、感受直接的“轻体验”。一张几十块的电影票,一次几百块的短途出游,一个价格合适的IP周边,一支现场制作的冰淇淋——这些能用较低门槛提升日常质感、带来小确幸的消费形态,或许最贴合他们当前“在务实中寻找愉悦”的状态。
我们认为,一个品类在县域市场的所谓“爆发拐点”,本质上是一个特定县城中少量的消费者做了选择,而在1813个县域中同步发生、广泛复制的结果。这也是县域市场的价值,依托规模效应,广泛分布的、萌芽的需求的聚合也有可能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力市场。
- 持续的效率升级
在县城30元人均客单价,我们吃到了门店现切的鲜牛肉火锅,看似破旧的门店,但是明档。这个和刚在广州吃的120元客单价的鲜牛肉火锅,还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当下县域市场的供给格局还是分化的。连锁模式在加速下沉,但在早餐、生鲜等依赖灵活性与本地网络的品类上,其效率往往不如个体户,主要因为三个结构性差异:
1.租金:个体户可通过摆摊或自建房实现近乎零租金。
2.人力:个体户是“自我雇佣”,人力不计为显性成本。
3.供应链:对于蔬菜鲜肉,县域“清晨采摘上午上摊”的短链流通,在新鲜度上优于连锁的全国仓配体系。
 无需租金的摊位和自建房,摄于广东清远佛冈
无需租金的摊位和自建房,摄于广东清远佛冈
县域的自建房,想造3-4层都行,还能出租,这给了一线没办法想象的便宜的居住成本。如果用UE模型测算,从客单价到收入,到毛利率,到人工和租金,这些要素在县城都被抽象化了,租金和人工的成本降低可以这么直接。
 店主本人看店,闲暇时在旁边看下棋并自得其乐,摄于广东清远佛冈
店主本人看店,闲暇时在旁边看下棋并自得其乐,摄于广东清远佛冈
 卖不掉的蔬菜再自家食用,卖菜既能赚取额外收入也能打发时间,摄于广东三坑镇
卖不掉的蔬菜再自家食用,卖菜既能赚取额外收入也能打发时间,摄于广东三坑镇
因此,效率型供给的机会,在于那些能找到“口味最大公约数”,并能用规模效应重构性价比的品类。
例如,奶茶、炸鸡、零食集合店等品类产品高度标准化、口味大众化。万店规模的采购,让连锁品牌能向上整合供应链、减少中间环节,从而获得显著的采购成本优势,最终在终端形成“优质平价”的竞争力。
这解释了为何蜜雪冰城、零食集合店能在县域快速渗透——它们通过极致的效率,提供了过去没有的“好而不贵”的选择。
2025年,11.5%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在零食集合店的购物频次有所增加,2022年,这一比例为6.7%。
一个议题:县域女性
在最后的部分,我们想超越短期的行为变化,探讨一个可能更具有长期价值的议题——县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将这一议题纳入商业观察,并非试图将“女性的自我意识”简单转化为消费标签,而是关注社会思潮的变迁,这往往是消费市场结构性变革的先声。
从分性别的收入来看,我们看到县域男性的收入分布更向高收入区间倾斜,而64%的县域女性的个人年收入集中在3.5万元以下(即月薪不足3000元),这一比例显著高于男性(43%)。并且随着收入等级的提升,性别差距开始扩大。在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区间,男性占比(29%)是女性的两倍有余(12%);在1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男性占比(11%)也接近女性的三倍(4%)。
但“收入瓶颈”并非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本质上是特定的家庭分工事实与固化的性别角色观念,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发展机会与薪酬回报的制约。
这次访谈的其中一位乡镇的女孩,她来自河南这个高考大省,是从100多万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到211的佼佼者。由于家庭的原因,需要照顾爷爷奶奶、做好弟弟未来出去打拼的大后方,所以她回到了乡镇。当说到她网上做的自媒体工作,做几年能够在杭州有7000-8000元月薪的时候,她觉得或许可能,但还是觉得自己的收入不会超过爸爸(10万/年)。在县域,受到人情社会牵绊的个体,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会更大。
但从田野调研及市场走访,我们在县域女性身上看到了自我意识的萌芽状态。这种对自我的期待与照顾,实践形式是多样的,包括生育后对回归工作的计划、拓展副业、保持学习与锻炼、悦己消费等等,我们的观察角度并非仅局限在支出转化上。
与一线城市女性群体不同,县域女性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意识,并非一种脱离家庭角色或追求鲜明独立的“自我实现叙事”。因此从消费心理的洞察上,对县域女性的照顾需要更贴近 “自我安顿” ,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在既定角色中安顿自己,而非冲破传统。
写在最后
这次田野调研,有一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对话想写在最后。
湖北石首县的受访人(回访) :“父亲现在在上海上班,以前在当地做司机,有个亲戚弟弟定居上海了,父亲这两年去上海做保安,5-6000/月,为自己多存一点养老金。”
湖南湘潭县的受访人(回访) :“我母亲和婆婆都是照顾家庭为主,公公去了广东打工,父亲在农村老家还劳作。父亲曾经生过病,治疗费用医保基本可以报销,我是希望他不要再工作了,但他总停不下来,还和我们说,‘要是这点活儿都不干了,我就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
这些微观的努力,时常在我们所处的视野之外。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但我们生活在一线,人际圈也在一线,社交媒体所看到的内容也是一个信息茧房。社交圈与信息流构筑的回音壁,让我们很难看见故事的全貌。正因如此,四年间两次深入县域才显得尤为必要。
此次重返的时间恰好在宏观经济的换档期。我们想,无论市场如何起伏、周期如何轮转,这种源于亿万普通家庭的微观努力,从未改变。正因如此,我们对中国市场始终抱有信心——这份信心不仅来自数据与趋势,更来自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活选择时,一种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最朴素的追求与努力。